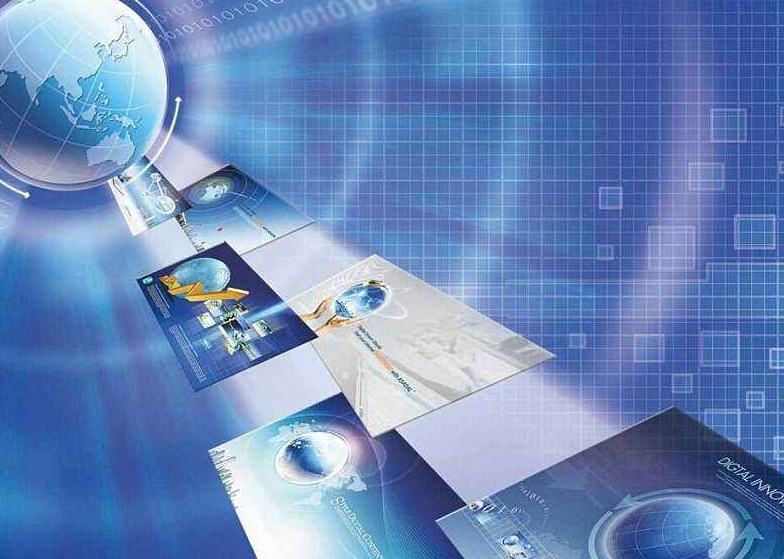
当然,作为极其古老的认识活动,史学一直是人类实现自我认知、达致群体认同的重要途径。在文字尚未发明的原始社会末期,随着部族联合体及早期民族的出现,大型史诗随之创生并广泛传诵,与神话一道建构群体内部的认同,从而维系了较大规模人类社会组织的存在与发展,并最终促成文明时代的到来。进入文明时代之后,史学更是在促成民族认同、价值认同、文化认同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社会作用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建构了以黄帝为中华民族共同祖先的起源话语体系,这一话语体系影响深远,其后拓跋鲜卑建立北魏,述其远祖即溯至黄帝之子昌意。班固在《汉书》中建构了一个五行相生、封闭循环的时间话语体系,将自太昊以来所有的正统帝王都纳入系谱之中。这一时间话语体系同样影响深远,之后的蒙元和满清,虽为少数民族所建王朝,但都自觉继承了为前朝修史的文化传统,其动因之一就是为了确立本王朝在这一时间体系中的位置。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风雨而能长盛不衰,发展成为当今世界规模最为庞大的民族共同体,离不开传统史学在推动群体认同方面所发挥的重大作用。显然,没有规模宏大的历史叙事,史学的社会价值便无从体现。乔·古尔迪和大卫·阿米蒂奇在《历史学宣言》中呼吁史学家们摆脱微观史学的狭隘局限,运用长时段思维,为人类思考现在及建设未来发挥独特的重要作用。
希罗多德撰写《历史》,兼记希腊人和异邦人的丰功伟绩,藉此颂扬乃至炫耀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曾经焕发出的勇气和荣光。司马迁撰写《史记》,更有着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”的宏大抱负。经典之为经典,除其事实详核外,更在于其文字之中处处渗透着对于人类命运的悲悯和关怀。大叙事需要宏大的形式和时空,但这两者都非其本质。大叙事之“大”,主要体现在史学家的人文情怀上。中西两大历史学之父早在两千多年前,就为史学家树立了伟大的人文情怀标杆。大数据时代,凡一切能够量化的学术技能,都有可能由信息技术全部或部分代劳,唯有人文情怀是人类主体性的最后营垒,技术无法染指。作为一门思考人类自身的人文学科,史学必须警惕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所导致的工具性话语霸权。如果不想失去在本学科领域的话语权,史学家就必须借助大叙事高扬人文情怀。唯大情怀者才能驾驭好大数据、利用好大数据,书写出真正关注人类过去、现在与未来的伟大叙事。